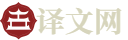(张爱玲)《封锁》
《张爱玲·封锁》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张爱玲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钉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 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他们有坐位可坐,虽然设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略胜一筹。街上渐渐的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 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还有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毅然打破了这静默。他的嗓子浑圆嘹亮:“可怜啊可怜! 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上了开电车的。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抱着胳膊,向车门上一靠,跟着唱了起来:“可怜啊可怜! 一个人啊没钱!”
电车里,一部分的乘客下去了。剩下的一群中,零零落落也有人说句把话。靠近门口的几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继续谈讲下去。一个人撒喇一声抖开了扇子,下了结论道:“总而言之,他别的毛病没有,就吃亏在不会做人。”另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说他不会做人,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
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妇把手吊在皮圈上,双双站在电车的正中。她突然叫道:“当心别把裤子弄脏了!”他吃了一惊,抬起他的手,手里拎着一包熏鱼。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看见了那熏鱼,就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 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 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裹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 然而无论如何,假使这封锁延长下去,耽误了他的晚饭,至少这包子可以派用场。他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半。该是心理作用罢?他已经觉得饿了。他轻轻揭开报纸的一角,向里面张了一张。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吕宗桢看着也觉得不顺眼,可是他并没有笑,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包子上的文章看到报上的文章,把半页旧报纸读完了,若是翻过来看,包子就得跌出来,只得罢了。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谷碌碌谷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老头子右首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
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了业后,翠远就在母校服务,担任英文助教。她现在打算利用封锁的时间改改卷子。翻开了第一篇,是一个男生做的,大声疾呼抨击都市的罪恶,充满了正义感的愤怒,用不很合文法的,吃吃艾艾的句子,骂着“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翠远略略沉吟了一会,就找出红铅笔来批了一个“A”字。若在平时,批了也就批了,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她不由的要质问自己,为什么她给了他这么好的分数。不问倒也罢了,一问,她竟涨红了脸。她突然明白了: 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
他拿她当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待;他拿她当做一个男人,一个心腹。他看得起她。翠远在学校里老是觉得谁都看不起她——从校长起,教授、学生、校役……学生们尤其愤慨得厉害:“申大越来越糟了! 一天不如一天! 用中国人教英文,照说,已经是不应当,何况是没有出过洋的中国人!”翠远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 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
翠远搁下了那本卷子,双手捧着脸。太阳滚热的晒在她背脊上。
隔壁坐着个奶妈,怀里躺着小孩,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这至少是真的。
电车里,一个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书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盹着的那个人。大家闲着没事干,一个一个聚拢来,三三两两,撑着腰,背着手,围绕着他,看他写生。拎着熏鱼的丈夫向他妻子低声道:“我就看不惯现在兴的这种立体派,印象派!”他妻子附耳道:“你的裤子!”
那医科学生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有一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将折扇半掩着脸,悄悄向他的同事解释道:“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行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
吕宗桢没凑热闹,孤零零的坐在原处。他决定他是饿了。大家都走开了,他正好从容地吃他的菠菜包子。偏偏他一抬头,瞥见了三等车厢里有他一个亲戚,是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儿子。他恨透了这董培芝。培芝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作为上进的基础。吕宗桢的大女儿今年方才十三岁,已经被培芝睃在眼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脚步儿越发走得勤了,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轻人,暗暗叫声不好,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若是在封锁期间和这董培芝困在一间屋子里,这情形一定是不堪设想! 他匆匆收拾起公事皮包和包子,一阵风奔到对面一排座位上,坐了下来。现在他恰巧被隔壁的吴翠远挡住了,他表侄绝对不能够看见他。翠远回过头来,微微瞪了他一眼。糟了!这女人准是以为他无缘无故换了一个座位,不怀好意。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微笑,随时可以散布开来。觉得自己太可爱了的人,是熬不住要笑的。
该死,董培芝毕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宗桢迅疾地决定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调情的计划。他知道他这么一来,并不能吓退了董培芝,因为培芝眼中的他素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老年人。由培芝看来,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是老年人,老年人都是一肚子的坏。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谁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他向她低声笑道:“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翠远吃了一惊,掉过头来,看见了他搁在她身后的那只胳膊,整个身子就僵了一僵。宗桢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自己抽回那只胳膊。他的表侄正在那里双眼灼灼望着他,脸上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如果他夹忙里跟他表侄对一对眼光,也许那小子会怯怯地低下头去——处女风的窘态;也许那小子会向他挤一挤眼睛——谁知道?
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他道:“您也觉着闷罢?我们说两句话,总没有什么要紧! 我们——我们谈谈!”他不由自主的,声音里带着哀恳的调子。翠远重新吃了一惊,又掉回头来看了他一眼。他现在记得了,他瞧见她上车的——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巧得到的,并不能归功于她。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的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 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包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 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 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
宗桢道:“嗯?”他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他眼睛钉着他表侄的背影——那知趣的青年觉得他在这儿是多余的,他不愿得罪了表叔,以后他们还要见面呢,大家都是快刀斩不断的好亲戚;他竟退回三等车厢去了。董培芝一走,宗桢立刻将他的手臂收回,谈吐也正经起来。他搭讪着望了一望她膝上摊着的练习簿,道:“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
他以为她这么年轻?她还是一个学生?她笑了,没做声。
宗桢道:“我是华济毕业的。华济。”她颈子上有一粒小小的棕色的痣,像指甲刻的印子。宗桢下意识地用右手捻了一捻左手的指甲,咳嗽了一声,接下去问道:“您读的是哪一科?”
翠远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潜移默化所致。这么一想,倒不能不答话了,便道:“文科。您呢?”宗桢道:“商科。”他忽然觉得他们的对话,道学气太浓了一点,便道:“当初在学校里的时候,忙着运动。出了学校,又忙着混饭吃。书,简直没念多少!”翠远道:“你公事忙么?”宗桢道:“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 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翠远道:“谁都有点家累。”宗桢道:“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翠远暗道:“来了! 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 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翠远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宗桢道:“我简直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家去。回到哪儿去。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他褪下眼镜来,迎着亮,用手绢子拭去上面的水渍,道:“咳,混着也就混下去了,不能想——就是不能想!”近视眼的人当众摘下眼镜子,翠远觉得有点秽亵,仿佛当众脱衣服似的,不成体统。宗桢继续说道:“你——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翠远道:“那么,你当初……”宗桢道:“当初我也反对来着。她是我母亲给订下的。我自然是愿意让我自己拣,可是……她从前非常的美……我那时又年青……年青的人,你知道……”翠远点点头。
宗桢道:“她后来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连我母亲都跟她闹翻了,倒过来怪我不该娶了她! 她——她那脾气——她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翠远不禁微笑道:“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 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出这句话来,伤了她自己的心。宗桢道:“当然哪,你可以在旁边说风凉话,因为你是受过上等教育的。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他顿住了口,上气不接下气,刚戴上了眼镜子,又褪下来擦镜片。翠远道:“你说得太过分了一点罢?”宗桢手里捏着眼镜,艰难地做了一个手势道:“你不知道她是——”翠远忙道:“我知道,我知道。”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翠远与宗桢同时探头出去张望;出其不意地,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
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
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话,关于他们银行里,谁跟他最好,谁跟他面和心不和,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他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瞧你这张嘴!”
宗桢沉默了一会,忽然说道:“我打算重新结婚。”翠远连忙做出惊慌的神气,叫道:“你要离婚?那……恐怕不行罢?”宗桢道:“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福。我大女儿今年十三岁了,才考进了中学,成绩很不错。”翠远暗道:“这跟当前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她冷冷的道:“哦,你打算娶妾。”宗桢道:“我预备将她当妻子看待。我——我会替她安排好的。我不会让她为难。”翠远道:“可是,如果她是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只怕她未见得肯罢?种种法律上的麻烦……”宗桢叹了口气道:“是的。你这话对。我没有这权利。我根本不该起这种念头……我年纪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翠远缓缓的道:“其实,照现在的眼光看来,那倒也不算大。”宗桢默然,半晌方说道:“你……几岁?”翠远低下头去道:“二十五。”宗桢顿了一顿,又道:“你是自由的么?”翠远不答。宗桢道:“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
翠远抿紧了嘴唇。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 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 气! 活该气!
车上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外面许是有了“封锁行将开放”的谣言,乘客一个一个上来,坐下,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
宗桢与翠远奇怪他们刚才怎么这样的糊涂,就想不到自动的坐近一点。宗桢觉得他太快乐了,不能不抗议。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不行! 这不行! 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你是上等人,你受过这样好的教育……我——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可不是,还是钱的问题。他的话有理。翠远想道:“完了。”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再也不会……呵,这个人,这么笨! 这么笨! 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希罕的一部分。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多么愚蠢的浪费! 她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式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向他解释有什么用? 如果一个女人必须倚仗着她的言语来打动一个男人,她也就太可怜了。
宗桢一急,竟说不出话来,连连用手去摇撼她手里的阳伞。她不理他。他又去摇撼她的手,道:“我说——我说——这儿有人哪!别! 别这样! 待会儿我们在电话上仔细谈。你告诉我你的电话。”翠远不答。他逼着问道:“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电话号码。”翠远飞快的说了一遍道:“七五三六九。”宗桢道:“七五三六九?”她又不做声了。宗桢嘴里喃喃重复着“七五三六九”,伸手在上下的口袋里掏摸自来水笔,越忙越摸不着。翠远皮包里有红铅笔,但是她有意的不拿出来。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
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他走了。对于她,他等于死了。电车加足了速力前进,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的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的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翠远烦恼地合上了眼。他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她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 她明白他的意思了: 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 一个人啊没钱! 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
1943年8月
在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中,张爱玲崭露头角,而《封锁》则是她稍后的一篇力作,发表于1943年11月女作家苏青主办的杂志《天地》第2期,曾收入张爱玲1944年9月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它的声誉虽不及《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中篇佳构,却一直被公认为是作者的短篇代表作。
张爱玲身处乱世,自己的命运也曾数度为战争所逆转(如1939年欧战爆发阻挡了她赴英伦求学的步履,因此改进香港大学;又如1941年底香港沦入日军之手,一份优等生的履历和保送牛津大学深造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于是被迫返回上海,卖文为生),却没有成为一位热血沸腾的抗战作家,她自称乐于描写的都是些“男女间的小事情”。这篇《封锁》把小说背景设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的一辆且行且止的电车上,所凸现的仍是张爱玲独具个性的人生体验——人与人的相识相遇是极其短暂和不可把握的。
“封锁”是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他们以清查抗日活动为名,经常在人口密集地区突然宣告封锁,只用绳子拦一拦,便有一大片地区断绝交通。这种“画地为牢”的暴政,使正好经过那里的行人,欲归不得,欲哭无泪。小说描写一辆普通的电车在行进中遭逢这种厄运,其意不在谴责制造麻烦的源头,而是着力表现电车上的乘客在非常态的时空内非常态的遭遇和感受。
“电车”是城市人几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因而也就成了城市的显著标志。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说:“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电车与“回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给她提供了一份难以替代的安稳妥帖。电车上的人临时组合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共向目标前进,而不久就要各奔前程。可是“封锁”使时间忽然停在链条的某处关节不再转动,临时性变成了一种假定的永恒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位由此开始。且看《封锁》中的众生相:
华茂银行的会计师、三十五岁的吕宗桢抱着奉太太之命买来的菠菜包子下班回家,电车一停,他忽然看到存心想要娶他大女儿的穷表侄也在车上。为了避免受到“进攻”,他连忙换到对面的座位上,旁边就是未婚的大学英文助教、二十五岁的吴翠远。接下来表侄发现了他,向他走来,他又只得慌不择路地与身边的吴翠远攀谈起来。从念的大学谈到专业,他又开始抱怨自己因包办婚姻娶来的太太,他们就这样由简单的调情发展到错觉在谈恋爱,他甚至已经表示打算离婚再娶。他向她要电话号码,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后来封锁结束了,他像条件反射一般迅速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她才猛然顿悟,“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一场似乎一见倾心的感情遭遇已如春梦了无痕迹。
吴翠远的生活经历十分简单,做好学生、好女儿、好老师,努力使自己格调高雅,端庄大方,却过分压抑了自己真实的精神欲求,是个公认的好人,却不是真的人,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如意,就是不快乐。而吕宗桢则从大学商科毕业,是个新式的成功男人,穿着西装戴着玳瑁眼镜提着公事皮包,有太太有女儿,什么都不缺。可是他也活得过于规整,潜意识中渴望着超出生活轨道的新奇和刺激。遇到一个能为他脸红的女人,他便从背负了数种责任的社会角色,摇身一变为“单纯的男人”。就这样,两人在一个非常态的时空中“敷衍”了一场恋爱,绽放出自己人生的另一种感情,然后迅速回到各自的生活常态之中。张爱玲极其擅长刻画两性心理,此篇中的情感冲突尽管较《金锁记》等要缓和得多,但仍表现得细致精微。
小说极富戏剧舞台式的场景效果,人物描写的层次感与立体感十分强烈。“封锁”以后,先是车外乞丐高声乞讨,电车司机闻声长叹。然后写到车内人们的表现,几个公事房的工作人员议论自己的同事,三言两语即现倾轧之意;一对中年夫妇,男的提着一包熏鱼,女的慌忙提醒他不要弄脏裤子,那种马上联想到干洗价钱的唠叨,惟妙惟肖地勾画出城市小市民的精明和琐屑。接下来男主角被推至前台,他孤单一人,只得无聊地读包裹包子的报纸,即使包子上印上的铅字是反的,他也逐个艰难地认清,于是认出了“讣告”、“华股动态”等用得着的字眼。在他的启发下,全车没有说长道短和吵架拌嘴机会的人们都开始读一切手边的印刷品来打发忽然静止的时光。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老头子没有从俗,只顾搓手心里的两只核桃。这便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过渡,因为老头子旁边坐的就是吴翠远,她利用封锁的时间批改学生作业。她隔壁坐的是一个怀抱小孩的奶妈……一圈主次演员悉数登场亮相,整个舞台已尽显饱满之态,故事这才进入高潮,男女主角因为穷表侄的偶然出现而纠结在一起。这种点与面相谐相和的丰满的舞台效果,集中体现了作者明确的场景意识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另外,这篇小说更运用了大量恰切的意象和隐喻来塑造人物性格。写那个揉搓核桃的老头子,他的光头就像一个核桃,而绝妙的是形容“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顺水推舟似的就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沉闷呆板。写吴翠远改着学生作业,却感叹着自己爬到了知识女性的顶端,可是当别人希望她当的好人太久了,并不真的快乐。隔壁奶妈怀里抱的孩子,脚心抵在她的腿上,她凝视着“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深感“这至少是真的”。最明显的要算是对吴翠远的精致刻画。她穿的是白洋纱滚蓝边的旗袍,“很有点讣闻的风味”,一方面突出了她表面上极端的冷淡素洁,缺乏女人味道,另一方面也和此前吕宗桢读到“讣告”相映照。她的头发梳得毫无特色,“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她的美也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一个长期压抑着内心欲求的形象跃然纸上。
机智而不动声色的讽刺也是张爱玲惯用的手法。在这篇小说中,尽管着墨不多,却也常常造成点睛之笔。如,医科学生画人体骨骼图,却被旁人误会是速写,一个个还煞有介事地评论着,提熏鱼的丈夫说:“我就看不惯现在兴的这种立体派,印象派!”人与人之间的认知竟错位到这种南辕北辙的地步,每一个个体的孤独感也就更加苍凉彻骨。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古译文网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