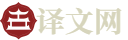再写几句
看过了《茶花女》,马彦祥先生要我写几句,我已写了一小篇了; 现在《北洋画报》又要我写几句,我只能写些零碎的小事了。
茶花女是动辄得咎的: 她要安心当她的婊子罢,人家说她没骨头,烂污货; 她要做个好人罢,人家不相信她,不肯答应她,结果是她死了。
排演《茶花女》也有些左右两难: 右边的人可以说:“这是什么东西,新戏总是要不得。”左边的人又可以说:“《茶花女》这种戏根本就可以不必排,至少也该让我们来排,不该给余上沅排。”
但《茶花女》终于博得了若干人的同情与眼泪,排演《茶花女》也终于博得了若干人的同情与眼泪,也就够安慰的了。
两位老先生在看完戏之后大发议论:
一位说: “茶花女尽美矣,未尽善也。夫既不惜一死,即当于杜父之前剖心以自明,而后乃成其为轰轰烈烈之奇女子。……”
一位说: “否,否,不然。使果死于杜父之前,天下后世将以杜父为何如人?其所以不即死,正所以全杜,亦所以全杜父,舍其所易,为其所难,此其所以为尽善尽美也。”
我对于这两位策论家的议论都能领悟与欣赏,但我却要摹仿旧戏里小丑的口吻说: “茶花女呀,您别在杜法尔面前死呀,死了咱们这出戏就唱不下去啦! ”
又有两位先生在戏场里谈天:“《茶花女》是林琴南译的。”
“不,这个戏本是什么复译的。”
“哦,我知道了,是严复,严又陵。”
“严又陵也做白话文么?”
“是,他做;林琴南可不干。严林虽然齐名,他们俩可要抬杠。”
哈哈!昨天我看见陈衡哲女士,谈起《新青年》时代的白话诗,她说“那是三代以上的事了”。征之于此,岂不良信。
赏析 《茶花女》是法国着名作家小仲马所写的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后改编为话剧。这部作品通过巴黎名妓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赞扬了玛格丽特的纯洁心灵,揭露了造成她悲剧的上流社会贵族、资产阶级的冷酷自私和道德的虚伪。《茶花女》问世后,受到法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欢迎。1926年刘半农把《茶花女》译成中文由北新书局出版,1932年在国内公演。公演后观众反应不一,刘半农有感于此,写《再写几句》。
《再写几句》第一节讲《茶花女》排演中左右为难之窘况以及演出的效果,大致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演出过程的扼要介绍。第二节、第三节是全文重点所在。第二节专写“两位老先生看完戏之后”的议论,作者撮取这一类封建遗老言谈的要点,不加评述,置于读者之前,孰是孰非,请读者公断。“两位老先生”以封建道德信条和伦理规范褒贬“茶花女”,这就远离原剧揭露资产阶级冷酷自私及道德虚伪的主题,《茶花女》被曲解了。第三节作者以简洁、传神的笔触描摹戏场里“两位先生”的随意对话,从中勾画出当时社会上不少人的一种心态。两位先生对《茶花女》译者的争论以及对严、林的评判,其愚妄和肤浅,一望而知。作者于此亦不加半点臧否,请读者自裁。结尾一段说开去,写作者同陈衡哲女士谈话提到《新青年》时代的白话诗,早已被人视做“三代以上的事”,十分遥远了,看去似乎离开了题目,但后文随即扣在题上: “征之于此,岂不良信”。作者感慨于早年曾经为之奋斗的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早被一般人淡忘了。
刘半农曾经是文学革命初期的战士之一,鲁迅曾经说他“很打了几次大仗”,所以他对于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旧观念、旧道德感受殊深,他痛感改造中国之不易,发而为文,是同他历来的思想相一致的。早在他译完《茶花女》之后写的该译本序言中就曾经说过: “中国的社会……说是旧吧,60岁的老翁也会打扑克,说是新吧,20几岁的青年也会弯腰曲背,也会摇头,也会抖腿,也会一句一 ‘然而’ 。实际却处处是漠不关心,‘无可无不可’ 。” 对于译介《天演论》、《原富》、《名学》介绍易卜生、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在中国看去,都好象是全没有什么。” “因此,《茶花女》在中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他却是希望人们“能够对剧中人的情事,细细加以思索”的。所以当话剧演出之后看到人们这种麻木、冷淡、任意曲解剧意的反应,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引起他深深的失望。从针砭旧中国凝滞、保守、落后来说,他是有道理的; 从对于一个曾经战斗过的勇士来说,他的心境未免有些颓唐。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刘半农个人的悲剧。
一
茶花女是动辄得咎的: 她要安心当她的婊子罢,人家说她没骨头,烂污货; 她要做个好人罢,人家不相信她,不肯答应她,结果是她死了。
排演《茶花女》也有些左右两难: 右边的人可以说:“这是什么东西,新戏总是要不得。”左边的人又可以说:“《茶花女》这种戏根本就可以不必排,至少也该让我们来排,不该给余上沅排。”
但《茶花女》终于博得了若干人的同情与眼泪,排演《茶花女》也终于博得了若干人的同情与眼泪,也就够安慰的了。
二
两位老先生在看完戏之后大发议论:
一位说: “茶花女尽美矣,未尽善也。夫既不惜一死,即当于杜父之前剖心以自明,而后乃成其为轰轰烈烈之奇女子。……”
一位说: “否,否,不然。使果死于杜父之前,天下后世将以杜父为何如人?其所以不即死,正所以全杜,亦所以全杜父,舍其所易,为其所难,此其所以为尽善尽美也。”
我对于这两位策论家的议论都能领悟与欣赏,但我却要摹仿旧戏里小丑的口吻说: “茶花女呀,您别在杜法尔面前死呀,死了咱们这出戏就唱不下去啦! ”
三
又有两位先生在戏场里谈天:“《茶花女》是林琴南译的。”
“不,这个戏本是什么复译的。”
“哦,我知道了,是严复,严又陵。”
“严又陵也做白话文么?”
“是,他做;林琴南可不干。严林虽然齐名,他们俩可要抬杠。”
哈哈!昨天我看见陈衡哲女士,谈起《新青年》时代的白话诗,她说“那是三代以上的事了”。征之于此,岂不良信。
(1932年12月1日《北洋画报》)
赏析 《茶花女》是法国着名作家小仲马所写的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后改编为话剧。这部作品通过巴黎名妓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赞扬了玛格丽特的纯洁心灵,揭露了造成她悲剧的上流社会贵族、资产阶级的冷酷自私和道德的虚伪。《茶花女》问世后,受到法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欢迎。1926年刘半农把《茶花女》译成中文由北新书局出版,1932年在国内公演。公演后观众反应不一,刘半农有感于此,写《再写几句》。
《再写几句》第一节讲《茶花女》排演中左右为难之窘况以及演出的效果,大致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演出过程的扼要介绍。第二节、第三节是全文重点所在。第二节专写“两位老先生看完戏之后”的议论,作者撮取这一类封建遗老言谈的要点,不加评述,置于读者之前,孰是孰非,请读者公断。“两位老先生”以封建道德信条和伦理规范褒贬“茶花女”,这就远离原剧揭露资产阶级冷酷自私及道德虚伪的主题,《茶花女》被曲解了。第三节作者以简洁、传神的笔触描摹戏场里“两位先生”的随意对话,从中勾画出当时社会上不少人的一种心态。两位先生对《茶花女》译者的争论以及对严、林的评判,其愚妄和肤浅,一望而知。作者于此亦不加半点臧否,请读者自裁。结尾一段说开去,写作者同陈衡哲女士谈话提到《新青年》时代的白话诗,早已被人视做“三代以上的事”,十分遥远了,看去似乎离开了题目,但后文随即扣在题上: “征之于此,岂不良信”。作者感慨于早年曾经为之奋斗的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早被一般人淡忘了。
刘半农曾经是文学革命初期的战士之一,鲁迅曾经说他“很打了几次大仗”,所以他对于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旧观念、旧道德感受殊深,他痛感改造中国之不易,发而为文,是同他历来的思想相一致的。早在他译完《茶花女》之后写的该译本序言中就曾经说过: “中国的社会……说是旧吧,60岁的老翁也会打扑克,说是新吧,20几岁的青年也会弯腰曲背,也会摇头,也会抖腿,也会一句一 ‘然而’ 。实际却处处是漠不关心,‘无可无不可’ 。” 对于译介《天演论》、《原富》、《名学》介绍易卜生、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在中国看去,都好象是全没有什么。” “因此,《茶花女》在中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他却是希望人们“能够对剧中人的情事,细细加以思索”的。所以当话剧演出之后看到人们这种麻木、冷淡、任意曲解剧意的反应,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引起他深深的失望。从针砭旧中国凝滞、保守、落后来说,他是有道理的; 从对于一个曾经战斗过的勇士来说,他的心境未免有些颓唐。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刘半农个人的悲剧。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古译文网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